2017年08月01日 10:38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作者:金灿荣 李燕燕
作者简介: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邮编:100872);李燕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872)。
内容提要: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蕴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战略博弈/功能性伙伴关系/共同演进
2016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出乎预料地赢得大选。考虑到特朗普竞选期间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立场,①一些人认为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将充满变数。但我们看待中美关系,不仅要看到领导人执政理念和风格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还要看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总体特征,更要看到国际发展的潮流趋势。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两国未来将保持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这不是任何单一领导人所能改变的,中美关系只能顺势而为,走共同演进、合作共赢之路。
一 中美关系的总体特征
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以来,国际格局发生巨变、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也是中美关系产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四十多年。中美两国在战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互相依赖、彼此合作又相互竞争,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复杂又极其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理解两国互动所蕴涵的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处理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
(一)中美关系在当今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美国因素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由美国强大的实力、影响力和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决定的。同时,作为多极世界中重要的一支力量,中国与美国已经形成利益捆绑与竞争关系,“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影响力的发挥、国家安全的保障都绕不开美国。近年来,中国外交注重经营周边,积极拓展“全方位外交”,但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与对美外交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联系。其原因在于:
1.国家层面: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最大的难题
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就双边关系而言,中美两国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中国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极为有限,而美国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近现代史与中美关系史的发展轨迹是几近平行的。这使得美国因素对中国的国内国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就国内而言,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的重要准则,中国尤为关注美国因素对中国政府维护政权的合法性、维护国内秩序的影响;②就国外而言,美国因素是中国外交布局上的重要考量。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四根支柱。在这其中,中美关系在整个中国外交布局中意义重大。这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毋庸置疑,而美国掌握中美关系更多的主动权。③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施加更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美国常以弱小国家庇护者或平衡者身份对中国形成掣肘,美国的态度和行为影响中国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中美在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影响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软实力;另外,美国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主导国,中国参与其中并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都绕不开美国。
2.体系层面:美国是中国外交最大的外部因素
国际秩序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秩序:“第一秩序”是指大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的秩序,“第二秩序”是指受此影响的各国国内政策选择。从第一秩序来说,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秩序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遭遇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从经济总量来看,中美经济领跑全球,中美两国与欧、日、俄、印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增大。从发展前景来看,尽管中国面临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等挑战,但总体上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与之相比,日本虽然从经济实力上仍然是多强中的一强,但体量更大的中国很容易发挥后发优势超越日本。从根本上说,日本与英、德等国都属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的“中等强国”(the middle powers),④无法与中美等国相提并论。首先,日本的产业已丧失了全球竞争力。二战结束后,发展钢铁生产是日本的基本国策。而半导体被视为“工业的基础”,所以日本政府也大力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日本的这两大产业都曾雄踞世界顶端,但以后再也没出现过日本主导发展起来的产业。日本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描绘未来的愿景。⑤其次,日本曾经在技术上领先中国,但这只是一种脆弱的优势,中国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在技术上拉平日本。一旦技术上拉平,中日之间的竞争将由规模来决定。而中国的工业化具有规模巨大、门类全面、体系完整的特点,是全能型冠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赶超日本成为必然。
欧洲国家近些年来同样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缺乏竞争优势的劳动者在外部竞争加强的压力下面临困境,英国脱欧成为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之一,这必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欧洲自由贸易进程将放缓,金融监管体系将受到冲击,甚至欧盟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拖累;二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恶化了经济形势;三是来自北非和东南欧洲的“难民潮”激化了社会矛盾。未来欧洲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聚焦社会治理,中欧关系将面临深化合作和构建全新双边关系的机遇,中国可以通过投资和金融合作“锁定”中欧战略关系,增强中欧之间要素流动的广度和深度,为建立亚欧大市场奠定坚实基础。⑥
俄罗斯的问题则在于,国内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是一个“单一作物经济体”(one-crop economy)。⑦从社会结构看,俄罗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出生率过低,2016年人口增长率是-0.06%。⑧目前,中俄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经济的互补性有利于提高双方的务实合作,发展稳定的双边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主要强国,或面临国内危机自顾不暇,或发展前景和潜力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从长期来看,中国将在未来的安全战略博弈中保持更大优势。而中美关系则与此不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正在逐年缩小。据世界银行测算,201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9万亿美元,中国则达到10.8万亿美元,⑨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在量上增长迅速,质上也有了突破性提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报告称,2015年中国专利申请总数首次在单一年度内超过100万件,这一数量几乎是排名第二、三、四位的美国、日本、韩国的总和。⑩随着中美两国实力水平的接近,利益互相冲突的增加,两国间的竞争也将进一步加剧。例如,在安全方面,特朗普竞选期间就宣称要停止削减军费预算并大幅增加美军舰船数量,尽管就目前而言,特朗普的这一计划能否成功受制于其能否在重振美国经济前提下确保有足够的资金保持预算扩大军备,但未来在安全方面中国需要提防美国军队继续在南海制造事端,另外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还有可能会在“实力求和平”的战略目标下纵容日本发展军备,增加自主空间,从而增加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压力。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如何定位是目前最大的难题,中国和美国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国际体系,中美关系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中美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如果中美两国陷入地缘斗争、军备竞赛或是零和对抗,那么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将岌岌可危。中美若能求同存异,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领域找到更广泛的共同语言,那么亚洲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前景都将得到增强。(11)
(二)中美关系:竞争且合作与重要又复杂
从历史上来看,中美关系历经风云变幻,从敌视、对抗到缓和、合作,其中突发性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但是,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将中美之间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如何客观看待彼此,对中美两国的精英与民众来说都是困难的,人们彼此欣赏,又对对方心怀忧虑。2016年美国皮尤(PEW)调查的一项数据说明,54%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在阻碍中国的崛起,而37%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军力增强令其担忧。(12)这种复杂心态,归根结底是由中美关系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1.中美两国关系是一对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如今的中美关系不同于过去美国与其他强国的关系。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以竞争为主,除了在军控方面保持脆弱的平衡之外,两国间的合作很少;现在的日美关系尽管在贸易、防务等领域存在分歧与矛盾,但两国之间是一对牢固的盟友关系,双方仍然以合作为主;中美关系介于两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将其称为“竞合关系”(coopetition),但最近合作与竞争的平衡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转移。(13)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关系可能会产生更多变数,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出现一定调整,未来美国可能会在经贸方面制造摩擦,在台湾问题上越界,在南海问题上获取某种优势及以朝核问题对中国施压。但是,台湾和南海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特朗普会认识到中国底线所在;贸易摩擦是双输战略,无益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强大”战略,朝核问题是挑战也是机遇,很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内容,因此,中美关系有很大的反复性,同时又有很强的韧性,所以过去我们经常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但现在有学者提出,从现在到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几年间,中美间会存在一个相互适应期,中美关系要么好起来,要么坏下去;要么深入开展合作,要么走向战略竞争。(14)中美之间存在冲突性因素,甚至有学者将中美这种既非冷战也非“热战”的关系称之为“凉战”。(15)
2.中美关系是一对重要又复杂的双边关系
就其重要性而言,正如上文所述,在某种程度上说,中美关系决定整个21世纪人类的命运,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不谨慎。就其复杂性而言,一方面,中美之间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2015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总额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16)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军事上、战略上互相视对方为竞争对手,在人类近代史上很少有这么复杂的关系。
从结构性特征来看,两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和冲突性。(17)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无可挑战的霸主地位,属于守成大国。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入世”推动下,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名义GDP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属于异军突起的新兴国家。中美这种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关系决定双方的战略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突性的。不仅如此,除了地缘政治与经济冲突,中美两国还存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冲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文明形态上讲,美国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国是儒教文明,两国在文明方面存在冲突的因素。因此,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两国间关系要更加复杂。
(三)中美关系:结构性对抗与利益捆绑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对抗来自中美两国实力变化所带来的客观结果。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矛盾、地缘政治矛盾、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以及台湾问题。(18)但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上相互联系,安全上面临共同威胁。中美两国开展多领域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双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防止世界经济出现问题,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稳定,防止埃博拉病毒扩散、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曾将中美这种复杂关系比作19世纪时期的“权宜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双方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必要结合在一起,即便互不喜欢也不得不维持双方关系。(19)
(四)中美关系发展受到诸多第三方因素干扰
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美关系在结构上是一种“外力推动型”关系,两国关系的起伏经常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第三者”的存在,(20)双边关系一直在这种变化中相互调适。抗日战争时期,为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中美形成了共同阵线;冷战时期,为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中美之间建立了“心照不宣的同盟”;(21)冷战结束后,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则建立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上,第三方因素成为两国建立密切关系的“黏合剂”,但第三方因素却也对中美关系产生干扰。朝鲜战争的爆发曾使中美两国陷入近二十年的敌对,而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菲律宾、越南、朝鲜、伊朗和缅甸等国家的影响,中美两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经常引发双方的互相猜疑,甚至有时产生摩擦。因此,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中美自身,而受到第三方的掣肘。(22)
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变化是近年来伴随中国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意图的担忧愈发明显。当前,美国国内掀起一场自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23)引发辩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一些美国学者与政府官员认为,过去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会带来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壮大的中产阶级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利,到那时中国就会从一党执政变成美国式民主社会。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水到渠成地促成中国的政治自由化,(24)中国从而将变成一个没有区域或霸权野心的西方式民主和平国家,这也是一直以来美国欢迎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和平、稳定”的国家的前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认为,中国的崛起为美国带来了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破坏者,中国日渐成为一个“通过削弱美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破坏美国的联盟,最终把美国逐步赶出亚洲,并将自身打造成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大国”,(25)美国过去几十年奉行的对话接触政策基本失败,未来美国需要大幅改变或调整对华政策,甚至有一些极端的观点主张美国应明确抛弃对华接触,在各个领域反击或制衡中国。(26)所以,在有关对华政策辩论中,美国对华遏制和敌对的思维有所上升。
二 中美安全战略稳定的发展机遇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给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带来了挑战。美国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的影响,而中国也面临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强大起来后不会延续“国强必霸”的逻辑,两国间战略信任下降,双边关系面临多重挑战,除了两国关于贸易、西藏、台湾、人权等领域的“老”问题,双方还在亚太地区领导权、中国军事现代化、新空间领域、海洋问题、中国发展模式等问题出现新的摩擦。(27)尽管两国之间依旧问题重重,但中美之间在文明、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相似的主体特征,面临完全不同于过去列强争霸的时代条件,享有保持战略稳定的历史条件,这使得中美两国能够建立一种有别于过去以“对抗和冲突”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双方把控分歧、避免冲突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一)老游戏新选手
第一,中美两国都是具有洲际规模的超大型国家,这意味着双方都不可能压倒性地征服对方。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大国政治模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在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中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一次正规战斗的军事实力。”(28)就规模而言,中美两国无论是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自然资源、生产能力、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因素,还是文化、艺术、社会吸引力等软实力因素,都在国际社会中首屈一指。相比历史上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德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都是“全能型冠军”,两国谁也不能征服或彻底摧毁对方,这构成了双方战略稳定的基础。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国际政治的进化,征服变得愈加困难,“共同生存”成为当今社会大国政治的主要特征,(29)对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中美两国政府与精英都认识到,两个超大型国家爆发大规模冲突或战争对于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此,即便双方出现摩擦或矛盾,双方都会尽量保持克制,避免冲突升级。
第二,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state),更具有包容性特征。“在成为民族国家之前,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实体”。(30)与历史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德国、日本相比,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儒家文明基础上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拥有多民族和平相处的悠久历史与丰富经验,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极具包容性。美国则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新教文明基础上的由多种族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熔炉”。中美两国都是在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对待文化的差异性时,更注重兼收并蓄;在进行政府治理时,更强调灵活多变,这些特质与文化种族同质性很强的民族国家截然不同。因此,中美两国的竞争,并没有像美苏争霸那样出现强硬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安全战略博弈,而是灵活多变,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又互有妥协,在处理诸如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一些敏感事件或突发危机的过程中避免了危机升级。
第三,中美两国文化上都具有多元性,尽管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大为不同,但都讲求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中美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是典型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而非“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互宽容性很强。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美国人不关心理论而偏重实践的实用主义特性,普遍爱好物质福利的物质主义特性以及坚定捍卫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个人主义特性,(31)正是这些特性成就了美国的强大与繁荣,并成就了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自豪感和优越感。同样,中国信奉的凡事可通融、可变通的处事哲学就是一种实用主义观,中国人更加重视现世生活而非将希望寄托于来世,这种物质主义观使得人们对世俗生活更加积极。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大多数民众具有一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就是强调艰苦劳动、积极奋斗和不断追求财富,(32)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讲求集体主义,但中国哲学中激励个人奋发图强、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思想也是注重个体意识的体现,所以才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尊重鼓励个体奋斗的思想。而伴随着财富的扩大以及私有,个体会有强烈的意愿去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因为只有和平的外交政策才会保障个人的获利。(33)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具有牢固的民众基础。
第四,中美两国都讲求软实力,重视文化认同,强调完善自身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美国自诩为“山巅之城”,强调自身的道德制高点。中国则崇尚儒家的“以德服人”和道家的“无为而治”,依靠以身作则和循循善诱来影响世界,(34)在遇到挑衅时能够保持克制,始终将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这与霸权国家喜欢四处秀肌肉、依赖强制与恐吓对待弱小国家、遇到冲突时往往反应过度的行为截然不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战术上保持有所作为的同时,还坚持战略上韬光养晦,保持克制。在应对美国挑衅时,除了被中国视作核心利益的台湾、海洋领土以及可能影响到中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问题,中国在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全球治理等问题上总体上还是采取刺激—回应式反应,尽量避免刺激美国,(35)这种“打太极”战略也经常让美国无计可施。
总而言之,在第一类机遇中,美国将中国视为现实社会的权力竞争者,却没有像过去的英国、日本和德国那样陷入冲突或战争,双方的游戏手法不一样,两国的竞争与过去的列强争霸迥然不同。
(二)老游戏新背景
第一个新背景是核时代条件下的“核恐怖平衡”。自人类进入核武器时代以来,核武器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将人类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推向极致。人类对有核国家“确保相互摧毁”能力的恐惧对于制约有核国家爆发战争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正是出于对对方核能力的恐惧而在处理双方矛盾和冲突时表现得格外谨慎。同样,中美都是核大国,虽然在核威慑方面是一对非对称关系,但双方都拥有足以彻底摧毁对方的核武库,同时,两国都是理性的负责任的行为体,任何一方都不会利用核武器来打破平衡或双方的“战略稳定”。
第二个背景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活动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全球化增强了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程度,各种利益交织,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双方形成一种天然的约束关系,任何针对对方的遏制或者孤立政策都会危害自己的利益。其次,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治理问题的全球化,单一国家无力独自面对气候、资源、恐怖主义、疾病控制等全球挑战,必须携手合作。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求重新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宣称要将制造业留在美国,但是其政策目标并非是反全球化,退出全球化只是美国谋取更大利润的筹码,美国据此要求更改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格局,以保证在全球化中获得最大份额,因此,美国不会放弃以其为主导的全球化。
第三个背景是两国市民社会正发挥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中美两国都拥有强大的市民社会,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推进,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和发言权逐步增强,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越来越大。两国民众都关注政府对于权利、义务和利益的分配,崇尚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的商业英雄。对战争的厌恶和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是市民社会的普遍特征。在美国,大量的社团和积极的社区活动对美国政治实践产生重要影响,(36)美国民众对小布什期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行为的不满和反战情绪使得奥巴马政府改变进攻性政策并减少对外直接军事干预。中国近几十年来城市化迅猛发展,市民社会发展迅速,媒体、意见领袖甚至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影响日增。社会公众天然地要求个人自由、幸福生活以及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中国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民众更加反对伤亡与战争,这也间接导致了过去十年里的参军意愿下降和军队兵源减少。(37)
第四个背景是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刚性化对大国冲突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首先,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的制度化进程加快,国家行为日益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约束,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法律法规对国家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特征,国家出于对违规成本、国际信誉等原因的顾虑,经常会自愿加入某些具有强制性或约束力的国际组织。其次,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倾向于用公开、公平、公正和更具权威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存在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平台。对中美两国间的某些矛盾和摩擦,各种国际法和国际仲裁机构为双方的仲裁或谈判提供了解决机制与途径,国家不必诉诸武力解决冲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为两国的贸易反倾销诉讼、知识产权纠纷等提供了重要平台。
第五个背景是国际政治“无政府文化”的进化有利于两国间的和平发展。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看来,无政府状态下有霍布斯式、洛克式、康德式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体系中大国间的相互关系分别为“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从国际关系发展史来看,美国自一战开始后介入国际事务,倡导去殖民地化,倡导法治,说服各国通过和平方式抢占世界市场份额,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实现繁荣,这无疑对于国际政治从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逐步转变为洛克式无政府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总量的一半,但它依然建立起开放的经济秩序,让其他国家得以繁荣发展并参与竞争。(38)二战后,美国主导与推动了欧洲复兴和繁荣,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持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正是在洛克式无政府文化下,世界各国越来越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非领土争夺上,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全球经济繁荣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的典型案例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两次崛起。第一次是二战之前,日本学习西方列强抢占周边地盘,侵略中国、朝鲜等国,掠夺中国台湾地区,还伺机征服亚洲大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因遭到美国的惩罚而最终失败。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则发生在洛克式无政府文化下,通过市场经济和法治力量,日本不断扩大在亚洲和全球的市场份额,实现了从士兵到优秀工程师的转变。因此,二战后美国倡导建立的国际社会总体来说是和平、开放和公平的,同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也受益于这一和平的国际环境。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必然以支持并维护这一环境为目的,中国没有理由去破坏或改变这一环境。
(三)中美关系中的历史遗产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现在,中美两国共同经历了冷战的结束和双边关系的突破,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复合性的一对双边关系,四十多年来,中美两国关系为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提供了五个历史遗产。
第一,中美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商品进口国和第三大商品出口国,2015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 980.7亿美元,(39)中国商品对美国进口额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5%,2007年到2015年,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FDI)年均增长12.2%,2015年FDI总额达到1117亿美元。(40)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虽然数量上低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但是近些年增长迅速,2015年对美FDI从2014年的119亿美元增长到150亿美元,(41)增幅达25.8%。同样,美国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2016年9月,中国持有美国1.15万亿美元债券,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者。(42)甚至有人将中美两国间的资金相互依赖现象称作“金融恐怖平衡”(the 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43)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使中美两国发展成一对“命运共同体”。因此,尽管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鼓吹要在当选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大幅提高关税,但上任后,特朗普及其顾问已经相对淡化了中美贸易战问题,当然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特朗普需要优先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以及调整与盟国或伙伴关系。因此,未来虽不排除中美关系会因贸易问题受到影响,但是,特朗普也应该认识到,将中国作为贸易惩罚的目标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大幅提高对华贸易关税至多只是将市场转移到其他经济体中,并不必然有利于美国制造业,何况提高关税只会损害包括美国企业主和普通蓝领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而后者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双边密切的经济交往将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尽管学术界也有人质疑贸易并不必然带来和平,甚至可能会成为冲突的根源,但相互依赖至少使得战争更具有毁灭性,因而相互依赖缓解了人们发生冲突的冲动,(44)成为促进和平的主要力量。
第二,中国和美国存在广泛的社会和人际往来。“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文化与人员交流可以缓解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并促进互信。目前,包括华侨在内的美国华人大概有六百多万,与在美的犹太人数量相当,在美华人具有很深的爱国情结,他们成为中美之间特殊的黏合剂。中美两国间大量的次国家行为体省(州)和城市还结成二百多对姐妹省(州)和姐妹城市关系,(45)这在一般国家是没有的,中美直接接触非常深入。不仅如此,两国人员往来密切,2015年,两国人员往来达到475万人次,2016年前三季度,中美两国日均往来人数达1.4万人,中国赴美游客人数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7%,美国来华游客增长7.3%。中国游客带来的直接就业机会4.5万个,间接就业机会23万个,而2016年11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尚不足20万。(46)另外,中美两国还互相举办中(美)国年、旅游年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人员往来与交流已经独立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并成为制约政治经济摩擦的“稳压器”。中美人文交流已经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共同构成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支柱,这为两国关系的长期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的民心保障。
第三,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美两国共同应对了很多挑战,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的范围、领域进一步深化。除了在反恐问题上开展合作之外,中美两国在伊朗核项目“5+1”谈判、朝鲜无核化问题等国际合作中取得成效。2014年,两国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一声明打破了几十年来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努力达成有效的全球协议上所面临的僵局,(47)中美的合作还为两国主导起草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巴黎协定》做出重要贡献。总体来说,中美双方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积累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这意味着中美“确立一个更加稳定、可靠的良性互动架构,开创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可能的和可行的”。(48)
第四,邓小平做出的正确战略选择。回顾中美两国和解之初,不难发现,共同反苏这一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则是与中国确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将处理对美关系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在一起,将建立稳定和平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49)基于这一判断,自邓小平时代开始,历届领导人关于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都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不另起炉灶,不试图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权威,选择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发展,这一决策为中美双赢与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中国的崛起正是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实现的,因此,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支持者、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50)中国的崛起对于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是一个新的变量,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是一个革命者,要主导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实际上,中国维护联合国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正如美国前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所述,习近平的对外政策虽然和前几任领导人相比大为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无论是能力和实力都与过去截然不同,但总体上依然延续了过去尤其是1978年后中国的发展路线。(51)
第五,中美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对话机制。中美两国已有上百个对话交流机制,(52)两国高级官员之间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彼此之间的联系甚至超过了美国与其盟友的联系。尤其是2009年两国在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基础上建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两国间规格最高、内容最丰富的对话机制。这些对话机制为双方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双方加深了解,减少信息不对称、管控分歧,控制冲突。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近些年的双边关系出现复杂化的特征,双方竞争加剧,在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双方矛盾和分歧的螺旋式上升,而且美国新总统的上任很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增加变数,但是因为上述机遇的存在,中美关系的总体框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流。2017年2月1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时强调,两国元首“认为中美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应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53)这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定下良好基调。
三 “亚太再平衡”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
自2009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实施战略收缩的同时推动将“亚太再平衡”政策作为战略政策调整的核心。这一政策调整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21世纪以来,全球权力格局不明朗,美国错误地卷入两场战争,随后又爆发金融危机,美国的软硬实力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在全球范围的优势受到影响,不得不实施战略收缩,同时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第二,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影响日增,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凸显,中国寻求建立更加对等的中美关系。第三,中美两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当前很多亚太国家在经济上受益于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安全问题上采取选边站队的战略,使得地区权力格局出现“双领导体制”。
按照美国的说法,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主要关注四个领域:加强安全、拓展繁荣、培育民主价值、推进人类尊严。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军事部署向亚太地区倾斜。2012年时任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式上宣布,至2020年之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使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战舰比例分别为60%和40%。(54)这打破了以往美国将主要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和中东的传统模式,用处理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美国还利用朝核问题与韩国在东北亚地区共同部署“萨德”系统,从而给近年关系转暖的中韩关系蒙上阴影。第二,经济部署向亚太地区扩容。美国极力推动亚太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本质是想搞一个贸易圈,把中国排除在外,加入的国家多为美国的盟国、军事伙伴或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孤立或遏制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但是,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个工作日便签署行政命令,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兑现了他的竞选承诺。第三,利用中国和邻国的矛盾,在中国周边制造麻烦。例如近些年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日本关系恶化,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第四,抓住机会影响中国。美国打人权与民主牌,强调美国价值观,并多次声明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但同时又反复强调中国的崛起应该“基于规则”,(55)即按照美国所制定的规则在国际体系内发展。
“亚太再平衡”政策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亚太再平衡”政策加重了两国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疑虑,中方将“亚太再平衡”政策视为美国围堵中国的一项策略,而美国则怀疑中国将付出更多努力将美国挤出亚洲的势力版图并最终取代其地区乃至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56)其次,“亚太再平衡”政策加剧了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两国间的安全困境升级,甚至在某些领域竞争出现螺旋式上升。最后,“亚太再平衡”政策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信任不足,出现疏离或偶尔敌对的安全困境。
但总体来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效果有限。美国在安全领域的所作所为给中国制造了一些麻烦,本质上却没有动摇中国的周边国家政策和亚洲外交布局。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国际政治竞争终究还是实力政治,美国虽然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自金融危机后一方面经济受到重大打击,复兴乏力,其实力无法与其对外政策的雄心相匹配;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极化现象严重,民主党与共和党派系斗争激烈,矛盾难以调和,双方妥协空间缩小,尤其是自2014年民主党失去了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严重降低了奥巴马政府的决策效率,使“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执行出现困难,甚至在个别领域出现“力不从心”的局面。第二,中国近年来充分利用后起大国的后发优势,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使领先国美国面临被动和竞争压力,同时中国加大外交战略布局,统筹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将解决国内问题与化解外交难题结合在一起,在“走出去”战略牵引下,构筑“一带一路”、两翼齐飞的地缘战略框架,从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57)
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未来“亚太再平衡”政策命运如何,目前尚不能确定。与此同时,特朗普要求其亚太盟友韩国和日本担负更多防务开支,这些言论表明,与其前任相比,美国外交政策可能会更加倾向“孤立主义”。特朗普上任后其政策的出发点将建立在“美国第一”而非“世界第一”上,因此会将更多关注点放在国内,首要解决非法移民和经济下滑等问题。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颁布移民禁令,这在国内外引起极大争议,美国地方法院以违宪为由宣布暂停执行这一法令,而特朗普为维护自身形象与权威必将坚持到底。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国内优先”政策对中国来说可能会成为突破困境实现弯道超车的另一机遇。
四 中国的长期外交战略
诚如上文所述,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更无有关国际治理的政策阐述,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呈现不确定性。但也应该看到,美国政治体制中蕴涵一种源于改革传统的强大内在韧性,特朗普势必会对美国的政策进行调整。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外交的长期战略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会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和持续性。就后者来说,这一战略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积极应对内部挑战
应对内部挑战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难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具有“内向性”特征,(58)即外交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政府权威。具体表现在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决策层的合法性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来说,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幅增长,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需求不振和产能过剩相互并存,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尚不牢固等挑战。国内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中国的软硬实力发展并拖累对外力量,中国就会变成所谓的“脆弱的超级大国”。届时就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所说,唯一能遏制中国的国家是中国自己。(59)未来,中国能否掌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国内发展,只有以内部发展为核心,提高国内治理的质量和水平,国内社会矛盾缓解、民众生活质量改善、政府廉洁高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才能真正崛起,才能在亚太以及全球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并获得更深远的影响力。
(二)在不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情况下积极扩大外交布局
中国外交的核心议题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实现自身发展,同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60)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外交战略体现并契合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面对新环境与挑战,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而努力成为国际秩序与国际治理体系的建构者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以国家利益为准则的、宏大的“以我为主”的外交布局。首先,外交政策布局更加注重自主性与独立性。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外交工作“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6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寻求在战略上“韬光养晦”,战术上“有所作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一系列新概念和举措的提出就是其体现。其次,外交政策布局体现对美国利益的尊重。“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将“相互尊重”——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作为这一新型关系的重要内涵。不仅如此,中国反复强调对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的尊重,中国还强调中美两国具有广泛的利益和合作空间,强调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离不开中美两国间的深入沟通与坦诚合作,(62)并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扩大合作面以合作的增量淡化竞争的存量
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6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在短期内实现社会巨变而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和经济动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改革是增量改革,而俄罗斯叶利钦的改革是存量改革。以20世纪国营企业改革为例,邓小平提出通过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搞多种经营,最终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促进了国企改革,同时由于民营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步上升,使国企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则直接造就了国家的动荡和社会制度的颠覆。
增量改革为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现在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因素非常广泛,有些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正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影响双边关系的竞争性因素,把中美两国的合作面做大做强,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再去解决竞争性分歧,就不会动摇双边合作的基础并引发关系恶化或动荡。
(四)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中美两国内部对于中国是否应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中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或者承担多大程度的国际责任,则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中国履行更多义务,承担更多责任。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正式提出了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64)尤其是2008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提出“中美国”(G2)概念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美国相当一部分人批评中国履行的国际责任不足,而且存在“选择性”,只履行那些对中国有利的责任。中国方面,一种普遍性的观点认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力有限,承担国际责任是损己利人的行为,另一种观点则将美国要求中国担负国际责任的做法视作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阴谋论”。
不过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环境、气候、核安全、重大疾病、反恐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其中,中国在核安全工作中与美国合作,承担了保证地区核安全工作的责任,中美核安全合作也因此被视作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领域最为成功的合作领域。(65)同样,在2016年举行的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与美国等国就落实《巴黎协议》达成一致,这些合作有利于同美国“分担责任”,从而减轻美国对与中国“分享权力”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也坚持透明公正,这对于坚持法治和程序透明的美国来说有利于增进彼此认知,减少对彼此意图的误解。
(五)扩大对美投资从下到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发展中美关系,重要的是拒绝零和思维,坚持互利共赢。近年来中国实力增长、产业升级以及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但总体来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中国则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正是实现双方优势互补的体现。BIT的达成将有利于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同时有利于带动美国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对美投资稳步上升,未来中国对美国公众、企业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将会随之增大。如果中国在美国每个国会众议院选区都有投资,同时这些投资都能发挥良好的经济效益,为美国社会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居民生活能够改善,普通美国民众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那么美国民众也会欢迎中国投资,而不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在经济文化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国”局面,就像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大量投资汽车工业一样,丰富的就业机会能使双边紧张关系降温并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积极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对美国的长期外交战略是“两条腿走路”。积极的一面是倡导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努力扩大两国的合作面,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消极的一面是管控危机,消除战略互疑,避免冲突与对抗。
五 中美关系新前景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没有固定的答案,既不能说中美必有一战,也不能说中美必定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双方能够做到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最终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也取决于双方领导人能否发挥主动性,抓住当前的机遇。现在双方精英层有一些共识,我们要在一些方向上共同努力,合作共赢。
在美国,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美国应与中国共同演进(co-evolution)。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美国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中国的崛起,同时中国也应该做出一些改变。具体做法是,中美需要发挥磋商传统和双边信任,共同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通过磋商维护两国共同利益,消除紧张全面提升双方合作框架,共建太平洋共同体。(66)这一思路在一部分美国精英层中很有市场。(67)值得一提的是,“共同演进”思想虽然还未在战略层面上实施,但已经在中美两国民间有越来越多的体现。2013年,中美两国关于“虎妈现象”的讨论就是例证之一。在教育上,中美两国都在向对方学习,取长补短,这就是共同演进。在文化、饮食和流行音乐上,中美两国都在共同演进。
本文认为,未来中美两国最有可能的前景是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或者是实现两国协调。所谓两国协调,源于19世纪初的欧洲协调。当时崛起的法国在拿破仑的率领下横扫欧陆,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欧洲国家在英国的领导下击败了拿破仑军队。战争结束后,列强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决定以协商的方式处理欧洲重大问题。欧洲人认为,大国之间需要确立底线,也就是控制矛盾,避免兵戎相见,同时在重要问题上选择合作,实现共赢。欧洲协调体制使欧洲维持了从1815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近百年的和平。
中美功能性伙伴关系与此类似。具体而言,就是说中美两国不以建立同盟关系为目的,但会在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具体包括:双方共同维持地区的实力均衡;共同应对威胁人类生存的跨国问题和全球问题;通过协商方式承担关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同时在有竞争的领域控制分歧,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都保持机制性的沟通,避免出现误判,增强战略互信;在此基础上,双方通过合作建立起的互信逐步扩大合作面,并最终解决两国间的深层次矛盾和争议。在这一点上,“功能性伙伴关系”与陆克文(Kevin Rudd)关于中美“同梦想共使命的建设性现实主义”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68)要实现这一关系到两国人民未来的历史使命,需要双方领导人拥有宽广的眼界和非凡的智慧,认识到两国友好的必要,并拿出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领导人那样的巨大魄力,携手合作,克服不断上升的互疑螺旋,引领中美两国共同走向繁荣与和平。
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期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存在的纰漏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例如,特朗普宣称要对中国收取45%的关税,并发动贸易战。他还指责中国在南海和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并称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参见Katie Zezima,”Trump:’Who the hell cares if there’s a trade war?'” The Washington Post,May 20,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06/05/20/trump-who-the-hell-cares-if-theres-a-trade-war/; Peter Navarro,”China’s State-Sponsored Cyber Attacks Must Stop,” The Globalist,May 30,2016,http://www.theglobalist.com/china-united-states-cyber-crime-politics/。
②王缉思、徐方清:《两个秩序下,中美如何共同进化》,载《领导文萃》2016年第5期,第27-30页。
③张睿壮、陈小鼎:《中美关系六十年的影响因素及其历史启示》,载《南开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8页。
④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158-169.
⑤[日]大前研一:《真实的日本》,陈鸿斌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⑥赵柯:《欧盟亚太政策转向“新接触主义”?——理解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行为逻辑》,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2期,第28页。
⑦Joseph S.Nye,”Donald Trump’s Foreign-Policy Challenges,”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onald-trump-foreign-policy-challenges-by-joseph-s–nye-2016-11.
⑧Russia Demographics Profile 2016,http://www.indexmundi.com/russia/demographics_profile.html.
⑨World Bank,”Data for China,United States,” http://data.worldbank.org/?locations=CN-US.
⑩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2016,” November 23,2016,http://101.96.10.63/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1_2016.pdf.
(11)参见[美]约翰·艾肯伯里:《中国的崛起、美国及自由世界秩序的未来》,载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黄富慧、洪漫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12)Richard Wike,”6 Facts About How Americans and Chinese See Each Other,”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3/30/6-facts-about-how-americans-and-chinese-see-each-other/.
(13)[美]沈大伟:《纠缠的大国:理解中美关系》,载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黄富慧、洪漫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14)陈健:《中美关系发展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153页。
(15)Noah Feldman,Cool War: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2013.类似评论还可参见陆克文:《中美应化解“凉战”》,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918。
(16)U.S.Department of Commerce,Census Bureau,Economic Indicators Division,http://trade.gov/mas/ian/build/groups/public/@tg_ian/documents/webcontent/tg_ian 003364.pdf.
(17)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4页。
(18)袁鹏:《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02页。
(19)Zachary Karabell,”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The Huffington Post,http://www.huffingtonpost.com/zach-karabell/china-and-the-united-stat_b_246602.html.类似评论见David Shambaugh,”China and the U.S.: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china-and-the-u-s-a-marriage-of-convenience/。
(20)牛军:《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21页。
(21)陈兼:《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含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79页。
(22)袁鹏:《中美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1期,第6页。
(23)国内对于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全面分析见刘彬:《“中国威胁论”的新翻版:对西方所谓中国“新盛气凌人论”的评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56-66页;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9-28页;李海东:《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载《美国研究》2016年第4期,第9-36页。
(24)John Hemmings,”What U.S.Policy Gets Wrong About China?”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at-us-policy-gets-wrong-about-china-14817.
(25)Aaron Friedberg,”China’s Challenge at Sea,”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5,2011,A17.
(26)在这一观点上代表性人物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和阿隆·弗雷伯格(Aaron Friedberg),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4,pp.371-410。
(27)金灿荣、段浩文:《中美关系的问题与出路》,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75-80页。
(28)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4,p.9.
(29)Tang Shipi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1(March 2010),pp.31-55,25.
(30)[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3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张杨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404、382页。同样美国也有大批信奉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等。
(3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6页。
(33)参见Patrick Mcdonald,”Capitalism,Commitment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6,No.2(May 2010),pp.146-168。
(34)[美]熊玠(James Hsiung):《中国第二次崛起及其对全球、地区秩序的影响》,载门洪华主编:《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35)Erwin Blaauw,”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China’s Foreign Policy——Has China Become More Assertive?” October 23,2013,https://economics.rabobank.com/publications/2013/october/the-driving-forces-behind-chinas-foreign-policy-has-china-become-more-assertive/.
(36)关于市民社会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更多分析参见金灿荣:《美国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初探》,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56-73页。
(37)参见《独生子女时代的士兵:他们弱到无法实现北京的军事雄心吗?》,载《南华早报》2014年2月6日。
(38)[英]罗伯特·卡根:《美国不再管世界秩序》,FT中文网,http://www.flchinese.com/story/001070241#s=p。
(39)此处第三大出口国是指以单一国家计算的,如果欧盟28国作为一个单位,那么中国是美国第四大商品出口国。
(40)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16 Annual Report,November 2016.
(41)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and Rhodium Group,”New Neighbors:2016 Update,” April 1,2016.
(42)参见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treasurydirect.gov/govt/reports/pd/mspd/2016/2016_oct.htm。
(43)David M.Dickson,”China’s ‘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 Against U.S.,” The Washington Times,July 28,2008.
(44)David M.Lampton,Following the Leader:Ruling China,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pp.5,7.
(45)Reta Jo Lewis,”State’s Lewis at China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ities Conferenc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09/20120912135883.html#ixzz4RJXTDfyZ.
(46)《日均1.4万人往来中美之间 民间交流的持久魅力》,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9日。
(47)《中美气候合作大突破:中国将建设碳排放交易体系》,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926/13996307_0.shtml。
(48)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49)牛军:《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22页。
(50)习近平:《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环球网,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5-09/7647903.html。
(51)Jeffrey A.Bader,”A Framework for U.S.Policy toward China,”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March,2016,http://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us-china-policy-framework-bader-1.pdf.
(52)《李克强:中美关系怎么样,美国商人心里最清楚》,人民网,http://news.ifeng.com/a/20160316/47893188_0.shtml。
(53)《王毅外长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439455.shtml。
(54)Leon Panetta,”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1a%20dialogue/archive/sldl2-43d9/first-plenary-session-2749/leon-panetta-d67b.
(55)Karen Parrish,”Carter,Admirals Take Questions on China at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4,2016,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791296/carter-admirals-take-questions-on-china-at- shangri-la-dialogue.
(56)Michael D.Swaine,”The Real Challenge in the Pacific:A Response to How to Deter China,”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5,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5-04-20/real-challenge-pacific.
(57)马小军:《201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战略轮廓呈现》,载《学习时报》2014年12月29日。
(58)牛军:《再探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8页。
(59)Joseph S.Nye,”Donald Trump’s Foreign-Policy Challenges,”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onald-trump-foreign-policy-challenges-by-joseph-s-nye-2016-11.
(60)陈积敏:《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新布局》,载《学习时报》2016年10月3日。
(61)《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1113457723.htm。
(62)何亚非:《中国布局全方位外交新战略》,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10期。
(6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64)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2005,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65)David Santoro and Ralph A.Cossa,Strengthening US-China Nonproliferation and Nuclea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66)[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页。
(67)For examples,Michael D.Swaine,America’s Challenge: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Lyle J.Goldstein,Meeting China Halfway: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4.
(68)陆克文(Kevin Rudd)提出,中美之间应该首先“现实地”承认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其次“建设性地”在双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并将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政治资本和外交基石,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强信任,最终解决那些暂时的和难以调和的争议。参见Kevin Rudd,”China under Xi Jinping:Alternative Futures for U.S.-China Relations,” CSIS Report,http://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50313_rudd_speeches.pdf。
原文链接:
http://ex.cssn.cn/zzx/201708/t20170801_3597609_13.shtml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金灿荣粉丝网 » 金灿荣 李燕燕: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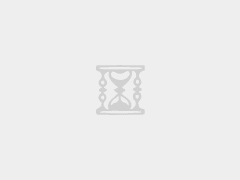
 最新很火的章文-金灿荣笑怼章文 :美国最恨中国的带路党 | 章文无言以对 (视频)
最新很火的章文-金灿荣笑怼章文 :美国最恨中国的带路党 | 章文无言以对 (视频) “政委”金灿荣:打贸易战,中国有五大优势,特朗普很可能估计不足
“政委”金灿荣:打贸易战,中国有五大优势,特朗普很可能估计不足 (强烈推荐)金灿荣-20180603讲座视频-中美关系与未来世界变局
(强烈推荐)金灿荣-20180603讲座视频-中美关系与未来世界变局